微信扫一扫

盐商后人姚以恩 扬州年菜记忆
盐商后人姚以恩 扬州年菜记忆
文化人姚以恩谈过年
盐商后人的扬州年菜记忆
在扬州盐商后人姚以恩的记忆里,过年很热闹。除了佣人备下包子、馒头、各色糕点用以“堆元宝”,他对家里过年煮的“全家福”印象最深。他记得家里有一只很大的紫铜火锅,用木炭烧火,煮“全家福”。姚家人丁兴旺,同居于扬州“打铜巷”里的祖屋,虽然到了姚以恩这一代早已各房分家,但同在一个偌大得院落里,好几个紫铜火炉同时翻腾着各色肉丸鱼丸虾丸、香菇、笋片,在一片热气蒸腾之间,觥筹交错,好一幅繁华喧闹的场景。
86 岁的姚以恩,江苏镇江人,曾长期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翻译家协会创始人之一。姚以恩还有另一个更为人知的身份,是圈内外著名的“吃货”,兼着几家著名淮扬菜系饭店的“顾问”。

文化人姚以恩谈过年
姚以恩的家,在上海茅台路上一个老式居民小区的高层建筑里。房子不算很大,胜在两间都朝南。其中一间是姚老先生夫妇俩的卧房,另外一间则俨然已被各色书籍占领得满满当当,从书柜到桌子、椅子、沙发、地板、冰箱、台几……老先生领着记者踮脚在书堆里走来走去,随手挪开一叠书,腾出一个椅子,示意我们坐下。
86 岁的姚以恩,江苏镇江人,曾长期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翻译家协会创始人之一、首任秘书长,上海文史馆馆员,《咬文嚼字》杂志编委。
“我的藏书,就是我的最爱,也是我最大的烦恼。说是最爱,是因为不论我处境如何,这些书总是我最好的精神支柱;说是最大的烦恼,是因为屋窄,我至今还不能把它们安置得井然有序。”姚以恩曾在自己写的一篇“藏心书屋琐记”中这样介绍。
姚以恩还有另一个更为人知的身份,是圈内外著名的“吃货”,兼着几家著名淮扬菜系饭店的“顾问”。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与扬州饭店创始人、有淮扬菜泰斗之称的莫有财私交甚笃,他后来帮着莫有财牵线搭桥到北京大开宴席,全城权贵富贾纷至沓来,莫氏后来以“姚以恩家宴”的名义专开一席,以感恩引荐之情。
姚以恩出生于扬州盐商之家,后虽家道中落,但自少年时养成的锦衣玉食,持续至今,成为日常生活里始终坚持的习惯。扬州盐商擅吃,已入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从小喜食荤腥,又以河鲜为美,吃菜离不开虾籽,食面以蟹黄佐之风味最佳。蔬菜则向来不喜,“鱼肉尽可穿肠过,绿叶蔬菜反而会引起肠胃不适。”
“打铜巷”里的年味
所谓“北京胡同扬州巷”,到了扬州,不得不逛的就是那些承载着浓浓旧时味道的巷子。扬州的老巷依托着著名的东西向旧城东关街为基准展开,东面直到当年隋炀帝开凿的古运河。明清时期,古运河的便捷为扬州带来盐业的商机,大批商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他们携家带口,在扬州求田问舍,沿着古运河修建大宅庭院,“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有人曾这样评论说,随便在扬州的巷子里走走,见到迎面走来的,或许就是旧时哪户盐商家的后裔。
在扬州旧城星罗密布的巷子里,有一条叫做“打铜巷”的小巷,巷子不足180 米,清代时由于巷内多制作铜质器具而得此名。姚家旧宅,就是在这“打铜巷”之中占据最显著的位置:“打铜巷3 号”。与巷子里其他明清时代建筑不同,姚家的宅院走的是半中半西式风格。最盛的时候里面有一百多间屋子,居住着这个姚姓盐商家族所有的成员。屋子与屋子之间有一道狭长的火巷分割,以防在发生火灾时可隔绝火势蔓延。而在平时,这道火巷则是分割主人与帮佣世界的分界线,姚以恩记得,沿着火巷一路走到底,便是佣人的房间,以及厨房所在地。
1928 年,姚以恩出生在这个宅子,是这个家族第四代的长房长孙。姚家的财富,由姚以恩的曾祖一手创立,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已算是扬州城里颇有家底的盐商世家,在扬州有钱号,在东台有盐垦公司。
扬州的盐商家族以擅吃闻名,姚家也无例外,凡是野鸭、蟹黄这类寻常人家桌上的珍馐,到姚家便成了稀松平常之物。
3 岁的姚以恩在扬州打铜巷姚家老宅前。作为扬州盐商后人,虽家道中落,但自少年时养成的锦衣玉食,持续至今,成为日常生活里始终坚持的习惯。
当时,正逢这个家族最盛的时期。姚以恩记得,自己当时时常被曾祖母牵着,去附近的富春茶社吃茶,五丁包子和野鸭包子是富春的招牌,也是姚以恩的心头所好,“可惜的是,现在野鸭都不许吃了。养殖的鸭子,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老先生儿时记忆里最念念不忘的味道,是来自一种叫做“桃花鵽”的野味。在辞海里,所谓“鵽”者,雉属,即“沙鸡”。但姚以恩记得清清楚楚,这种只有每当春天桃花盛开季节在江苏高邮地区才会出现的水鸟,嘴长,腿也长,且肉质细腻,香气四溢与一般沙鸡有天壤之别。这种春天里必吃的美味,如今已是全无踪影,姚老一日读书,看到作家汪曾祺一篇谈论记忆中美食的小文,其中亦谈到“桃花鵽”,称其为最鲜美之味,遂哈哈大笑,“看看看,原来那个姓汪的馋鬼也吃过哩。”
许是平日里就已经吃得极好,姚家的年菜反倒是显得中规中矩而没有更为奇突之处。
按照旧时习俗,过了冬至,家家户户便要准备开始过年。扬州人家在春节到来之前,要忙碌的事情很多,且都冠以“年”子来应景,《真州竹枝词引》这样记载,冬至前后所腌咸货(编著:鸡,鸭,鹅),至时煮之,曰“煮年肴”;庖人请伙来帮忙,曰“帮年”;祭灶后开发年事,曰“年帐”;族戚寒素者送以炭赀,曰“年敬”;往来馈赠者,曰“年礼”;神祠烧香,曰“年香”。
扬州的各种“年事”里,最重要的便是“年蒸”。所谓“年蒸”就是蒸点心,节前蒸好,存放在家中预备节日期间享用。姚家的“年蒸”从冬至腊八就开始了,姚以恩还记得,家里佣人把蒸好的包子、馒头、各色糕点,稍稍晾干,整整齐齐垒成一座小山,还要在其中缝隙之处用红枣等各种干果塞得严严实实,取其名为“堆元宝”,象征招财进宝。看着这座“元宝山”越垒越高,姚家的年味也越来越浓。
堆好的“元宝”,要放置在家中醒目的地方。除夕之后,正月里,各户人家串门,便是将这些“年蒸”之物按份取下,当点心给客人食用。
虽然姚家人不喜食素,但按照扬州人过年的传统,有几样蔬菜是除夕年菜必备。其中一味“十香菜”,寓意“十全十美”,由十种以上的蔬菜炒制而成(咸菜,百叶,豆腐干,萝卜,黄芽菜,香菇,酱瓜,酱生姜,水芹菜等)。不知道是否扬州人太爱追求“十全十美”,扬州人凡做此菜,都起码有一脸盆之多;蔬菜里,扬州人还讲究吃水芹菜和豌豆苗,芹菜因为中空,所以可取“路路通”的谐音;而豌豆苗,在扬州土话里被称为是“安豆”,有“安安稳稳”之意。
除此之外,扬州名菜煮干丝也是年菜中的必备。讲究的扬州人家干丝吃法,与我们现在知道的略有不同,是讲究季节性的,不同季节与不同的食材相搭配。春季河鲜上市,吃虾仁什锦干丝,还要点缀上开洋、鸡丝等;夏季黄鳝最为肥美,取鳝背肉佐以干丝;秋高气爽之时,正是吃蟹的好时候,就连干丝都要做蟹粉的来吃,而到了隆冬过年的时候,冬笋上市,年夜饭桌上就会出现一碗加冬笋丝的干丝。
“全家福”,则是除夕夜里姚家人年夜饭里的明星。上海“南伶”酒家主厨景国勇师傅后来告诉记者,扬州人过年,讲究的是八个冷菜,四个炒菜和六个大菜,其中“全家福”是大菜中的主角。
所谓的“全家福”就是扬州人吃的杂烩,里面有鱼圆、肉圆、虾圆、肉皮、蹄筋、笋片、鹌鹑蛋、香菇等不一而足,“越是有钱的人家,放到全家福里的食材就越好”,景师傅这样说。相比食材,姚以恩对“全家福”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家里有一只很大的紫铜火锅,用木炭烧火。木炭火力大,铜又传热快,不多久,锅内的汤头就翻腾得很热烈了,大人小孩争相将筷子深入锅中,捞那些先烫熟的东西来吃。
姚家人丁兴旺,虽同居于“打铜巷”里的祖屋,但到了姚以恩这一代早已各房分家,所以除夕并不聚在一起吃饭。试想一下,在一个偌大的院落里,好几个紫铜火炉同时翻腾着各色肉丸子、香菇、笋片,在一片热气蒸腾之间,觥筹交错,好一幅繁华喧闹的场景。

扬州名菜煮干丝是年菜中的必备。
上海岁月里的扬州美味
可是这场繁华很快随着年味散去。从极盛到衰落,姚家仅仅走过十数年光景。1937 年,日本人开进了扬州城,很快姚家的府邸被日本人占了去,家里各房一户户地被迫迁出,直到最后被完全清空。曾经空气中都透着温暖食物气息的“打铜巷3 号”变成了令人闻之色变的地方。
迁出大宅后,姚家人的生活也彻底落寞了,“起初,就是依靠一件件变卖家里的各种物件度日。”后来,值钱的东西也没了。16 岁那年,通过舅舅的关系,姚以恩来到上海,进了位于四川路上的一家叫做“宝康银行”的小钱庄做练习生。“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工作。”姚以恩说,当时的上海,扬州人最多做所谓“三把刀”(编著:剃头刀,菜刀,扦脚刀),均属比较低下的工作,相对来说,去钱庄上班被视作一项美差。
在钱庄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还算不错,可以攒下一些钱,接济家里。“每月领了钱,几乎全部都要寄回扬州家里。”姚以恩回忆。
当时的上海滩钱庄,老板会多请一个烧饭师傅负责给公司员工做饭。宁波路上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荣氏家族的产业,大老板荣毅仁是无锡人,由于特别欣赏扬州厨师莫有财的一道蜜汁火方,就在银行大楼旁给莫师傅置下一套房子,帮他开了饭店。交换条件是,莫师傅得天天给他银行里的高阶雇员做饭。
莫有财后来成为“淮扬菜泰斗”,他当时的这个小餐厅也成了姚以恩在上海常常光顾的地方。每当思乡情切,他就去莫家厨房打打牙祭,吃几道地道的家乡菜肴。一来二去,姚以恩和同为扬州人的莫有财熟了起来。这个昔日盐商家族里的少爷,懂吃却不会做,于是便乐得做一个口头司令,将儿时记忆中的美好滋味,一一复述出来,再由厨师加以还原。
比如扬州名菜“蜜汁火方”,“莫家菜”传人景国勇师傅如此介绍这道名菜。火方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原料,莫家菜的传统是只采用来自金华的火腿,因为只有金华火腿用的是金华两头乌。一只十二三斤重的火腿,只取中方一段作为火方食材,皮朝下放在砧板上,用刀剞小方块,深度至肥膘;之后,皮朝下扣在一个空碗里,加入清水,上笼蒸2 个多小时;取出加入冰糖、清汤再蒸1 小时;取白糖莲子再上笼蒸,最后放置旺火上,放入松子仁炸至金黄,倒入卤汁加蜂蜜,用水淀粉勾芡,放入糖桂花搅和,浇在火方上,并撒上松子方大功告成。景师傅说,蜜汁火方制作工序繁复,口味重甜腻,曾深受淮扬一带老吃客们的青睐,也是大户人家年菜中必不可少的一味。
还有一道淮扬名菜“海底松”,老先生姚以恩也是记忆忧新。取陈年的海蜇,去泥沙,再浸泡一天,然后切丝,放在大汤碗里,取用小菜心像削铅笔一样削尖,放在开水锅里氽一下备用;在锅里放入清鸡汤,烧开后倒入装有海蜇丝的大汤碗,然后把菜心朝上放在海蜇丝的周围,配以熟火腿片。因为海蜇头的形状酷似“松树”,也就成了这道菜的名字来源。
遗憾的是,“现在再来做,即便是知道步骤,总也做不出当年的那个味道了。”姚以恩表示。
不仅是“海底松”、“桃花鵽”,越来越多昔日姚家饭桌上的美味几近失传,或者貌合神离。最简单的例子,姚以恩嗜蟹,往往每当蟹季来临,他总归要吃上十轮螃蟹,每次四只,双雌双雄。他抱怨说,如今的螃蟹越来越没有蟹味道了,“以前吃完,螃蟹的腥气是很难去除的,非得依靠香菜末等反复洗手才行。而现在,吃完螃蟹,用水一冲就洗干净了。”
扬州菜的讲究,多是源自盐商在其后的推波助澜。扬州城里著名的典故,一个穷书生,娶了一户盐商家里的婢女为妻,一日,书生想要吃一个韭黄炒肉丝,妻子笑了笑说,如是按照旧日里的方法,估计你是吃不起的。按照她的做法,是要十个猪脸,取其面肉,炒成丝的。后来总算做成了,书生连赞好吃,把自己的舌头都吞下去了。
这个故事的真伪已不可考,对于姚以恩来说,他记忆中关于扬州美食的传说却实实在在曾经存在。
姚以恩记忆中的年夜饭菜单
首先是“年蒸”,姚家的“年蒸”从冬至腊八开始,家里佣人把蒸好的包子、馒头、各色糕点,垒成一座小山,取其名为“堆元宝”。其次是“十香菜”,寓意“十全十美”,由十种以上的蔬菜炒制而成(咸菜,百叶,豆腐干,萝卜,黄芽菜,香菇,酱瓜,酱生姜,水芹菜等)。第三是扬州名菜煮干丝,这是年菜中的必备。第四是年夜饭里的明星“全家福”。“全家福”就是扬州人吃的杂烩,里面有鱼圆、肉圆、虾圆、肉皮、蹄筋、笋片、鹌鹑蛋、香菇等

姚以恩年轻时和妻子的合影。
人物
名片
姚以恩,1928年生于扬州,毕业于上海俄专(上海外国语大学)后留校任教,著名翻译家,《列宁全集》60卷本定稿人之一。曾任上海翻译家协会首任秘书长,中国译协第二届理事,上海市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等,专门研究翻译犹太文豪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现任《咬文嚼字》、《世纪》终审编委。
初冬的上海,已略有寒意,茅台路高层建筑上的那豆灯火,远远望去,有一种温暖的向往。满头银丝,笑容亲和,85岁的姚以恩,说起话来,总是停不下来。正如他所致力翻译的肖洛姆·阿莱汉姆笔下的“领唱人佩西的儿子莫吐儿”一样,絮絮叨叨的话语中,总是饱含着快乐的元素。
1
生在锦衣玉食之乡
少时经历颠沛流离
熟识姚以恩的人都知道,若是和他在一起吃饭,蔬菜之类的最好别点,肉食则是多多益善。已过耄耋之年的姚以恩,养生之法似乎异于常人,鱼肉尽管穿肠过,可若是多吃了绿叶蔬菜,反而会引起肠胃不适。
这样的饮食习惯,是从幼年起就养成的。从记事开始,姚以恩的生活堪称“锦衣玉食”,姚家是盐商之后,哪怕祖父、父亲都没有工作,还是不愁吃喝。家里也有长辈在东台开了盐业公司,支持过新四军的革命事业。作为长房长孙的姚以恩,又是极受呵护,顿顿都是食不厌精。“归雁鸣鵽,黄稻鲜鱼。”《南都赋》中的“鵽”,可是姚以恩儿时餐桌上的至尊美味。野外打猎的野鸭,秋季熬制的蟹油,寻常人家难得品尝的稀罕食材,在姚以恩看来都是平常。
姚以恩至今还记得,家里宅院深深,房屋足有百间之多。长辈们出门,专门有两辆黄包车候着。两位车夫,分别叫做小谢和福子。姚以恩最快乐的玩乐,就是坐在黄包车上,用脚蹬踏车上的铃铛,一路清脆,招摇过市。家宅附近有间百货公司,调皮的姚以恩曾骑着脚踏车,一下子撞碎了店面玻璃橱窗,百货公司的经理闻声而出,吓得连忙抱起他:“小少爷,吓着了没有?”
生活极尽奢华,却没有让姚以恩沾上富家子弟的恶习。相反,在学业上,他一直都是非常勤勉。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功课向来很好,他还拿出一份中学时所写的《国学笔记》,上面毛笔写成的蝇头小楷,工整有序,字迹清秀,姚以恩至今保存,还笑称这是一份“传家宝”。
可惜,随着日军的铁蹄踏上中国大地,童年的美好时光戛然而止。时局动荡,家里也从原来的打铜巷,搬到了糙米巷,家中的日用开支,也是一落千丈。因为长辈们没有工作,加快了坐吃山空的速度。16岁那年,姚以恩就只身来到上海“讨生活”。
经人介绍,姚以恩进了一家小型银行做练习生,生活当然没有那么讲究了,甚至连晚上睡觉的床铺,都是在营业厅里支起一张钢丝床将就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时候的中国,安放不下一张酣然入睡的床铺。青少年时期的姚以恩,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上海的银行关闭了,就去了蚌埠、南京等地,四处谋职,只为一口饭吃。解放之后,他才又回到了上海。
2
生活艰苦不忘求学
参加国庆五周年国宴
就算是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里,姚以恩也没有放弃过求学之心。在各地工作时,只要是有些闲暇的时间,他都会捧本书在手,只有将目光和心情都沉积在字里行间,才能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
当初报考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时,姚以恩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轨迹的决定。对于当时的姚以恩来说,报考这所大学的最初目的很简单,其实就是有地儿睡,有饭吃,有学上,足矣。
学校里根据学员们的俄文基础,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在此之前,姚以恩并没有学习过俄文,但是天资聪颖的他,对于语言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天赋,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能用俄文写日记了,很快就从初级班,晋升进入速成班。
在这段时间内,有一件让姚以恩特别难忘的事情。1954年,他被派到北京俄语学院进修。因为中文底子好,主攻俄译中。也就是那一年,姚以恩和同学们,被授以光荣任务—在9月29日的国庆晚宴上承担翻译工作。当天,他们穿着制服,来到了北京饭店大宴会厅门口,远远就看到周恩来总理已经等在那里迎宾了。
好不容易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学生们特别激动,都想冲上去和周总理握手。但有人关照他们说:周总理接待外宾忙不过来,大家不要和周总理握手。于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崇敬地向总理点头示意,依次走进宴会厅内。当姚以恩走到周恩来跟前时,听到周总理说:“你们可以陪外宾跳跳舞嘛!”姚以恩停下了脚步,回了一句:“我不会”,周总理笑道:“小鬼,还不会跳舞?”
求学过程中,时任学校校长的姜椿芳,很快就注意到了姚以恩这位聪慧勤勉的学生,《文汇报》有一份《俄语周刊》,姜校长就让姚以恩代他去编,锻炼他的俄语水平。姜椿芳平时授课不多,但是他所上的翻译课,必定是学生们争抢着来听的。每当姜椿芳授课,都有一位女学生前来,就坐在姚以恩的同桌。她叫张茜,是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夫人。
没过多长时间,姜椿芳就被调往北京,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时,姜椿芳每次来到上海,都要找姚以恩陪同他去访问《全书》的编委和作者,甚至将办事处设在姚以恩家中。姜椿芳在北京筹建了中国译协,他授权姚以恩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翻译家协会,由姚以恩担任首任秘书长。
“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幸运能遇见姜椿芳老师,他对于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做学问一定要精确客观,待人接物则要仔细周到,这些都让我获益匪浅。”姚以恩感叹道。
3
《汉俄字典》让苏联人购买
定稿《列宁全集》编列宁家谱
毕业之后,姚以恩留校任教。除了正常上课,他还参与了很多重要文献的编译工作。编纂《汉俄字典》是一个耗时多年的文化工程,姚以恩参与其中,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文革”发生后,姚以恩被下放到安徽凤阳干校劳动。因为身患冠心病,所以也没让他做过重的劳作。有一天,他忽然被从上海来的工宣队员接回了上海,也不说是为什么。到了上海才知道,是要他看《汉俄字典》的校样,因为他对于文字的认真考究,那是出了名的。
1977年,《汉俄字典》正式出版。因为质量上乘,前苏联就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汉俄字典》。
姚以恩所做的另一项重要编译工作,就是参与定稿60卷本《列宁全集》。和《汉俄字典》相比,这份工作更需要加倍的耐心。比如在列宁的很多书信中,人名并没有写出全称来,这就需要姚以恩大量阅读,分析信件内容,来确定收信人的确切信息。为此,姚以恩特地编写了《列宁家谱》,这对于研究列宁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在外文中,一些亲属都用一个单词来概括,如舅舅、伯伯、叔叔、姨夫,都是一个“uncle”。如果这样翻译,对于很注重家族关系的中国读者来说,必定是一头雾水。姚以恩就用《列宁家谱》理清了列宁的家族关系。
4
翻译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
被称犹太作家的中国知音
在翻译界,姚以恩被称为“犹太作家的中国知音”,这和他长年以来,一直研究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肖洛姆·阿莱汉姆是乌克兰的一位著名文学家,他的小说和契诃夫、马克·吐温齐名。而在中国,首先研究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的,就是姚以恩。
早在50多年前,姚以恩收到翻译家李俍民的信,邀他翻译《莫吐儿》。当时的姚以恩,从未听说过这部小说,对于“肖洛姆·阿莱汉姆”这个名字也感到特别陌生。然而,当他一口气读完该书的俄文版后,立刻被其中引人入胜的故事深深打动。读完小说之后,姚以恩立刻开始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自己常常被文中的语言逗笑,有时又会伤感落泪,忽笑忽泣,不能自已。中文版《莫吐儿》出版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一股热潮,很多读者都被故事中的“莫吐儿”所吸引,来信纷至沓来,让姚以恩深受感动。
然而,姚以恩对于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研究并非止步于此,在1994年举行的“犹太人在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姚以恩就以自己对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研究作了精彩演讲。此后,很多犹太人都知道了姚以恩,不断有犹太人来到上海,想要和他见面。在这些来访的犹太友人中,最让姚以恩难忘的就是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外孙女贝尔·考夫曼。她也是一位作家,来到上海后,她紧紧握住姚以恩的手,感谢他在宣传自己外祖父作品上所作的贡献。而姚以恩自己也曾出访过乌克兰、波兰、加拿大、美国等地,都是为了探访肖洛姆·阿莱汉姆当年走过的足迹。
去年5月,国内首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研究中心”在南京大学挂牌成立,姚以恩出任中心主任。在成立仪式上,姚以恩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夙愿,如今终于得偿所愿,个中滋味,说与谁听。
5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交往巴金钱钟书茅盾等人
姚以恩一直认为,若是说他把《莫吐儿》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如说《莫吐儿》让他结缘了很多朋友。其中,就不乏丰子恺、萧乾、钱钟书这样的大家。其中,和一代文豪茅盾的交往,也是始于《莫吐儿》。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姚以恩在徐家汇藏书楼查阅那些灰尘蒙面的旧报刊。他忽然在一份报纸的副刊上,看到一则百余字的报道。报道中写道:“现代犹太小说家阿尔秦,被人称为‘犹太的马托温’。这个阿尔秦的作品和马托温一样,思想也相像。”报道末尾署名为“P生”。报道中的“阿尔秦”和“马托温”,其实就是肖洛姆·阿莱汉姆和马克·吐温,这让姚以恩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可能是中国最早介绍肖洛姆·阿莱汉姆的文字。
这段文字究竟是谁写的呢?姚以恩多年寻访,始终都没能搞清,但是他通过一些猜测,认为“P生”可能是茅盾先生。他尝试着给茅盾先生写信请教,茅盾回信才得以证实:“信上提到的‘P生’就是我。”至此,真相终于大白。
在姚以恩的治学生涯中,和很多大家都有着极为深厚的交往。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他的话来说,他和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写上一本书。


长按三秒识别关注
编辑 姚 波
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
展示家族的辉煌历史 助于激励子孙继往开来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3室2厅 3800元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70㎡| 2室2厅 1600元 面议 -

润泽悦溪
黑龙江70㎡| 2室2厅 2800元 面议 -

润泽悦溪
黑龙江85㎡| 2室2厅 1300元 面议 -

诗景长安
福建86㎡| 2室2厅 1500元 面议 -

领秀慧谷
海南88㎡| 2室2厅 8000元 面议 -

国风上观
黑龙江86㎡| 2室2厅 5000元 面议 -

新龙公寓
黑龙江88㎡| 2室2厅 6500元 面议 -

国美第一城
黑龙江86㎡| 2室2厅 2800元 面议 -

诗景长安
河南86㎡| 2室2厅 5500元 面议 -

山水家园
黑龙江88㎡| 2室2厅 6000元 面议 -

千禧家园
福建88㎡| 2室2厅 6000元 面议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4室2厅 250万 面议 -

青年汇
河南70㎡| 2室2厅 120万 面议 -

新龙公寓
海南140㎡| 3室2厅 160万 面议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2室1厅 160万 面议 -

远洋山水
河南80㎡| 2室2厅 160万 面议 -

国风上观
河南160㎡| 4室2厅 170万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85㎡| 2室2厅 150万 面议 -

诗景长安
福建70㎡| 2室2厅 150万 面议 -

远洋山水
河南160㎡| 5室2厅 300万 面议 -

领秀慧谷
海南140㎡| 3室2厅 160万 面议 -

新龙公寓
海南140㎡| 4室2厅 115万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50㎡| 1室1厅 49万 面议
自定义html广告位
-
下一条:陇西三秦王——后秦姚氏编年史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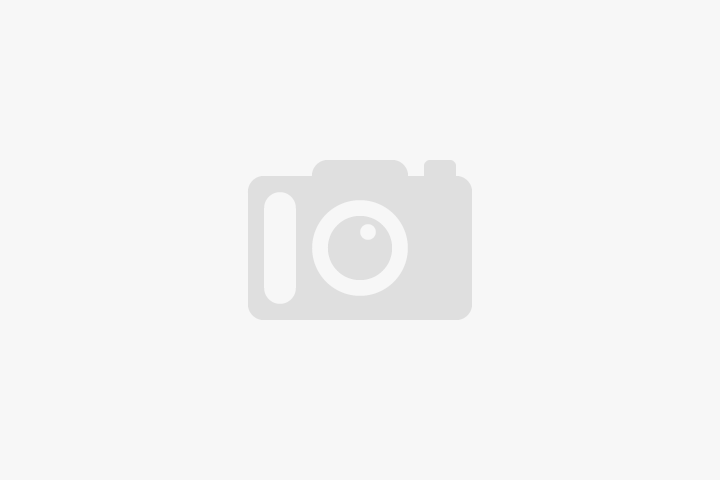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