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扫一扫

我眼中的大屋里头——姚燮故居之陈年旧事
我眼中的大屋里头——姚燮故居之陈年旧事
2007年12月2日下午5时,家父不幸辞世。不久,将母亲接到镇海居住,故乡老屋之门随之关闭。我是很少回去的,去了也只是个满怀痛楚的匆匆过客。老房子整修诸事一直由母亲打理。
前不久,老家一位热心人电话相告,打破了我原本的波澜不惊。她在电话里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北仑区领导和专家,已经多次到姚家斗“姚家大屋”进行实地考察和专门论证,你家的老房子是“姚燮故居”,政府准备予以修缮保护,具体方案正在酝酿。
说实话,此类说法早就有的。比如某高中同学用“羡慕嫉妒恨”的语气说,他家里会读书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是姚燮后代,我在报纸上看到过的。听完此话,我一笑了之。要说会读书,此话不假。我姐以下邵小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镇海中学,也是那年下邵公社考进镇海中学的唯一。吾儿步嬷嬷后尘,亦在镇中修习。就连我这个最不喜欢读书的,后来心血来潮,通过几年折腾,也拿到了“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但光凭会读点书就硬要与“浙东杜甫”姚燮去扯上关系,岂不是玷污先生寒碜自己?
听完老家热心人言之凿凿的话,不免心动起来,于是上网查询相关信息,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关于此类的消息还真不少,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被晒在网上,竟然被认定为“姚燮故居”。
想起卞之琳的那首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那些专家、学者、城市声像志愿者饶有兴趣地在明堂察看,透过紧闭的门窗洞察。而我,这个掌握钥匙的房屋主人却浑然不知,俨然是个局外者,通过照片中已经静止的画面才得知,原来我的老家曾有过几番热闹,这颇具黑色幽默。
历史是什么?历史如同这门和窗,当它紧闭之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平面,一幅静态,而历史原本是立体的,是动态的。
所有线索似乎在指向一个论点,我家与姚燮先生有着某些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不免心怀愧疚,不胜惶恐起来。后人告慰先人,应做到两个传承,既物质和精神的传承。可惜,祖屋没有用心保护和良好修缮,现已陈旧不堪;本人已年近知天命,无所建树。静心思之,有何脸面来应对先人询问?
可最起码应尽我所能,把“大屋里头”一些陈年旧事讲出来,我认为,这是应有的责任。遗憾的是,父亲已驾鹤西去,由他老人家来叙述将更有权威性。无助的我,只有凭记忆,把父亲告诉我的和我从小到大的些许琐事作一些回顾,以及家里保存下来的先辈画像、老式家具等拍成照片一并奉上,或许对研究姚燮先生的有关部门会有所帮助。
客观而言,“姚家大屋”这个称谓有点书面化。按照父亲说法和我的记忆,无论是乡里乡亲还是住在里面的,都不是说“姚家大屋”,而是说“大屋里头”。比如别人介绍我,肯定是这样说的:“这个小歪是姚师傅儿子,大屋里头的。”说“大屋里头”时并没有“羡慕嫉妒恨”的味儿,只是出于一种尊重。你瞧,大墙门是头部,傲视着正南方,前明堂后明堂以及四周木料砖瓦构成的房子,是庞大的身子,它如同一头雄狮傲然挺立在姚家斗这块风水宝地,怎不令人肃然起敬?而住在里面的我们,默默沐浴着它的熏陶,没有一丝傲气。我们和非“大屋里头”孩子一般的贫穷。
先祖最早建成“大屋里头”时,它的结构是“四明两弄”。也就是说,里面有四个明堂,两条弄堂,这两条弄堂,可不是概念中房与房、墙与墙之间的弄堂,而是房子中间的过道。无论外面下多大的雨,在这两条弄堂里行走,你可以不用撑伞坦然踱步。
可叹的是,在那个如火如荼年代,历代传承的家谱,被工作组搜出付之一炬。大墙门的两扇门,也被某位“破四旧”颇有领悟的村民卸下,移作搭建猪圈之用。幼小的我,常在夜深之时,听到那个掉了门牙狮头的呜咽。
当大墙门的两扇门和后明堂的两扇门紧闭之时,对外人来说,“大屋里头”俨然是一座城堡或者是一个迷宫。而幼年的我却穿梭在里面,乐此不疲。那时的我,一点都没感觉建造之美,而是一种兴奋一种好奇。我可以迈出家门,穿过一道道木质的门,进入一个个玩伴家,这无疑是件惬意的事。究竟是进入了大房家还是二房家抑或四房家,这不关我事。
邻里之间走动聊天是常有的事儿,不像现在住在所谓城里的我,一个小区甚至一个楼梯的,住了许多年还是相互陌生。吵架不愉快也很正常,就如夫妻间为了一句话而大动肝火。一家与一家为了一只鸡一条狗就吵了起来,于是把脸绷得紧紧的,住在“大屋里头”的当然也不能免俗。大人之间吵架,难受的是我们这些小孩,原本好好的玩伴不得不表明立场,大人在场时只能相互眨眼用以表达情感。逮住个大人不在的空闲,说话也不敢大声,更无法畅谈,特务之间联络暗号似的,轻声嘀咕几句就逃之夭夭。吵架后的“邦交”恢复正常,有时快有时慢,但总归有解冻一天。那时,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我们这些玩伴相互拥抱在一起,如同失散多年的亲密战友。
朝、志、秀、祖、大、常、允、秉、丞、继,这是记录下来的辈分排行,也就意味着再下一代过世,姚家已无相对应的辈分,除非再造。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多次与我提及,咱们家隶属三房,或许这个三房的划定应该从我的阿太算起。当我趔趄学习走路时,阿太还能蹒跚走几步的,也许那时候我有过这样的疑惑,阿太走路怎么和我一样的?说不定还偷笑几声呢。当我能跑时,阿太却躺在床上再也不会走了。
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太公。父亲说,连他也没有见过哩。太公去世得很早,爷爷和爷爷的哥哥——大爷爷,靠缠着小脚的阿太一人拉扯大,可以想象阿太的那个艰辛。
阿太住在朝南的那间。爷爷在外工作,很少回家,就算回来了,也是在外间的一张临时床铺凑合一夜,第二天又匆匆离去。父亲、母亲、姐和我四人住在里间。记忆中阿太睡的那张床边,还摆放着一个黑漆漆的棺材,其实这是寿材,可我哪懂这个道理,常常被它吓得要命,以至于每次生病发热,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个黑漆漆的棺材半浮在半空。
棺材是陪着我长大的。阿太冰冷的身子,躺入那冷冰冰的棺材悄然消失后,棺材并没有彻底消失。每年总有一些棺材送来摆放在堂前,过个一两天,在明堂入殓后搬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堂前就在我家的斜对面,正对着大墙门。一看到两张篾席悬挂在堂前,我心里就颤抖一下,一场盛大的“演唱会”即将举行。
幼年时,晚上一听到哭声,就往母亲的怀里钻。稍大时,父亲用他粗糙的手抚慰着我。一个人睡,害怕了就只能捂着被子想其他的事。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哭灵真算得上是一门功夫,两长一短、三长一短,我以为完了,结果她来个五长一短,把人等得,真叫那个心急。这个短还带一个钩的,属四声里的上声,把人的心撩拨得七上八下。有时候等着连续,结果等来的是间歇性断气,正为她担心,想不到她缓过来又唱出了高音。父亲故去,来了一帮专业的,就简单多了,那些人非常与时俱进,一边放《好人一生平安》《血染的风采》《真的好想你》等自以为符合场景的音乐,一边跟着节奏咏叹一番,少了几许真情实感。
阿太其实很疼爱姐和我的,只不过我们年少,哪知道她的这份怜爱。那时,阿太已经到了吃啥啥没味的年纪,故而在她的枕边总有一些小糖、糕饼之类的食材,那是大爷爷孝顺她的。她看到姐和我在房间里晃荡,偶尔会撩开蚊帐,伸出干枯的手甩出两块小糖或者糕饼来,我们俩既怕又馋,两眼散发着小鼠般的绿光。阿太故意把脸转过去,等到我们捡起地上的美味,一溜烟逃跑时,阿太就捂着嘴吃吃笑了。
我不得不提到大爷爷,我们三房后代能够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与他老人家的付出有着莫大联系。他年少到上海闯荡,凭自己的聪明和毅力辛苦打拼,终于,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站稳脚跟。人到中年,当上某烟草公司的总会计,还拥有一部分股权。家里有一个被敲掉一角的玻璃烟缸,在诉说着大爷爷曾有过的辉煌。
可惜大爷爷后来不幸得病,只能从十里洋场回到江南水乡,靠每年的固定分红来维持生计。不久,爷爷失业,父亲也失业,阿太、大爷爷、大奶奶、大爷爷的儿子、女儿、爷爷、父亲、母亲、姐姐和我,一大户十张嘴赖着大爷爷吃喝。大爷爷充分发挥总会计的精打细算,不至于让我们饥寒。在外人看来,我们的生活还相当的体面。
据父亲说,大爷爷回归故里的那段日子,与村民们经常玩一种“挖花”游戏,与现在风行全国的麻将差不多,不过在玩时是一边玩一边唱的。大爷爷很是狡猾,要是一直赢,就没人陪你,也就丧失赢的机会。他总是赢两次输一次,输的数目多少也是事先打好预算。大爷爷每天有件必干之事——对香烟的排列组合,他将两包香烟拆开分别装入烟盒,一支“飞马”一支“雄狮”然后又是一支“飞马”……村民到他这里聊天时,他拿出一支“飞马”给村民,很自然地在旁边拿出一支“雄狮”自己抽,村民以为他抽的也是“飞马”。这说明大爷爷的生活已经陷入拮据的困境,但他的腰板还是挺直。
大爷爷育有一儿两女。儿子是个痴儿,大爷爷过世没多久,突然癫狂自杀。大女儿眼白与眼珠有些不成比例,嫁了个矮骨隆冬黑不溜秋的农民。小女儿集成了大爷爷和大奶奶的所有亮点,聪慧漂亮,后来远嫁上海。我读小学时他们夫妻俩来过我家一趟,那时,大爷爷的小女婿已经是某国企的总工程师。
对于爷爷,我总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年少时起初是淡薄的,后来是忿怒的。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多了份理解,多了份内心的愧疚。爷爷是终老在敬老院的,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到敬老院去看他,连他离开这个尘世时也没有去送他。倘若坚持的话,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阻挡的。可惜,我没有。
幼年的我,站在河埠头旁,看着爷爷骑着自行车从对岸的那条河边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当爷爷不再在我的视线出现时,那条路变成了田埂,春夏碧绿,秋冬枯黄。
大年三十晚上,爷爷和父亲在昏黄的美孚灯旁,面对面坐着喝酒,姐和我能收到爷爷准备好的崭新的十张一毛。这个快乐能维持一个晚上,第二天枕头下面的美梦会被母亲悉数收藏,可我俩依然开心。
爷爷这一生其实是很苦的,老了还是孤苦伶仃。也许父亲去看他的,但父亲在家从不提起此事。年轻时爷爷总是间歇性地失业就业再次失业。父亲四岁时,爷爷的妻子,父亲的阿姆,我无法谋面的阿奶,因生育血崩而亡。可叹的是,父亲的妹妹在世的时间仅为几个小时。父亲为人老实,性格懦弱,晚年时一回忆起往事时常流泪,或与幼年丧母有关。
爷爷的身边隐约有个离婚的女人相伴,爷爷从未把她带回家,要是他坚持要与那女人结婚,父亲和母亲是无法阻拦的,可爷爷没有。爷爷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是下邵农机厂跑外勤。他基本住在宁波的旅馆里,父亲偶尔会带着我去看望爷爷。我见过那女人几次,现在已毫无印象。那女的见我们俩过去,默默点头打过招呼后,悄悄出去买来酒菜又无声无息离开。幼小时令伙伴们眼红的高档玩具,比如火石枪和小轿车,均出自爷爷的大手笔。
爷爷出事时,父亲已经是下邵农机厂的师傅,我和姐还未读书。爷爷跑外勤亏空了一千多,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巨款,爷爷无力偿还,提议抵押外间朝南那间房屋给厂里。厂里和父亲商量,要么父亲买下,要么卖给别人。村里的好事之人已经放出风来,愿意一千二买下。
父亲后来对我说,那时候他好几次想到了自杀。
父亲背上有两大压力,一个是心理上的,身为师傅,在徒弟面前抬不起头来;另一个是债务,一千块钱到哪儿去找?亏得徒弟有钱的出钱,没钱的紧跟着父亲,怕他一时想不开。软弱的父亲看着年幼的姐和我,咬牙迈过了这道坎。他变卖了家里的一些家具。请人拆下一些用来支撑阁楼的横条卖掉。现在还能清晰看到那时横条离开楼板的痕迹。父亲提议,不够部分每月从工资里扣除,厂里出于同情,答应了这个请求。父亲那时候是下邵农机厂工资最高的一个,加上加班月收入近五十块,厂长也为此眼红。省吃俭用,三年后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爷爷自打出事那天起,再没有踏进家里一步。我永远失去了爷爷。
在下邵乡上年纪人面前,提起父亲的名字也许不大知晓,可只要说到“姚师傅”,很多人是知道的,这源于他所掌握的两门技艺。父亲既是“小五金”师傅,又是“修钟表”师傅。故乡的一些老人这么记挂,恐怕更多的原因还是父亲留下的口碑。
由于家境原因,十三岁的父亲小学还没毕业,就匆匆背着行囊到上海学生意。靠大爷爷介绍,在上海“亨得利”钟表店做学徒。靠聪明勤奋,比其他师兄弟提前满师,正想大展宏图,想不到解放后,变成了下放工人。到首都没有站立之地,到江淮也不是长久之计,无奈回到故乡。在下邵农机厂做师傅期间,不管是谁做他的徒弟,都倾囊相教毫无保留。
小时候,我对父亲是非常佩服的。他小学没毕业,居然将图纸画得规规矩矩,成了实际上的下邵农机厂工程师,只不过那时候没有这一说罢了。戴上一个特制的放大镜,捣鼓着罢工的手表,让它“咔嚓咔嚓”再次摆动起来。别说装了,叫我拆开,也无从下手。
后来为补贴家用,又干起修钟表的行当。父亲出于面子,总说算了算了。村民也很纯朴,既然“姚师傅”不肯收钱,就送点种上来的东西吧,故此,我们家虽然没有一分地,蔬菜还是不大需要去菜场买的。
那时的师徒关系纯粹得要命。我和姐嚷着要到镇海看电影,父亲微微一笑,好吧,我派车,口气大得似乎他领导着一个“奔驰”军团。父亲一出口,呼啦一下,明堂里出现了十辆自行车,争着吵着抢着把我和姐朝自行车上拉,一支车队就浩浩荡荡朝着镇海进发。
父亲四十岁时,他们厂里的几乎都来了,还有乡里乡亲的也来了,在前后明堂、自己家里、隔壁邻居家办了十几桌,而所有酒菜费用酒席程序都是徒弟们一手操办的,提猪头的、拎蹄髈的、挑酒坛的、担熟食的,场面蔚为壮观。那些叔叔、伯伯也坏,一个劲灌我,几杯下肚,搞得我在河埠头前不停打转,把母亲吓得,赶紧拉我回家。躺在床上,我看着一会儿顺时针,一会儿逆时针旋转的楼板,嘿嘿傻笑。
我的童年虽然清贫但很快乐,这个快乐是院子赐予的。院子很小,就老屋到河埠头那点距离,十平米左右吧。父亲请人堆了些卵石在河埠头旁,将院子围起来,中间有一个通道,用竹篱笆作为门,向村民无声宣布,这个院子是我们家的。院子里种了棵水杉树,一年一年长了起来。母亲看地空着颇为可惜,就种了些向日葵,看着一张张向着北京天安门的笑脸,勾起了我强烈的种植欲望。在那片地里,我种过茄子、西红柿、花生、南瓜、冬瓜等各式各样的植物,均宣告成功。在我的眼里,结出果实就是成功。尽管西瓜只长出一个,拳头般大小,舍不得吃,后来烂了。
最快乐的是春夏之际。花开了,蜜蜂来了,蝴蝶来了,蜻蜓来了,蚂蚱在叶子周边跳跃,螳螂在树上爬行。我和父亲合睡的那张床蚊帐顶上,停着蜻蜓,挂着螳螂。起初,父亲默许了我热爱生物的良好行为。我以为这是父亲对我的一种鼓励,于是,蚊帐上的数量越来越多,品种愈来愈杂,蚂蚱也加入了这个阵营。父亲有些怕了,照这个事态发展,说不定哪天,麻雀、青蛙也要在蚊帐里与我们共眠。他坚决有力地将我心目中的宝贝清理出去,放送到院子里,并勒令我再也不许在蚊帐上投放半只。
穿过那道竹篱笆,就是用整块青石堆砌而成的“清爽埠头”,有左右两个,左边的那个朝东前行三米,还有一个做工相对差点的埠头,名曰“肮脏埠头”,专门用来刷马桶、荡痰盂的,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无文字记载,然而没有一个村民逾矩。
四十年前,那条河是非常清的。就算雨后河水溢上埠头台阶,假如某位村妇洗碗时不小心滑手,一眼望下去,亦能清晰看到它停留的位置。
某年夏天,父亲突然将我和姐扔到河中央,我俩吓得要命,不停呛水不断划拉。刚到父亲跟前,父亲又再次将我俩甩出。就这样几次后,我和姐学会了游泳。按照父亲理念,农村的孩子必须学会游泳,至于姿势无关紧要。是呵,生存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是花架子。
有人曾送给父亲三只小鸭子。父亲用篮子提回家后,我欣喜若狂,搬起锄头在院子里挥汗如雨,刨了一个很大的坑,又拎起铅桶到河埠头提了一桶桶水倒在坑里。我不停地倒,水不断消失。父亲不理解地看着我说,干吗?我说,让小鸭子在小池塘里戏水。父亲叹了口气,捧起三只小鸭子出去送给别人。为此,整整三天,我和父亲没说一句话。父亲用他质朴的行为告诉我一个道理,制止过热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源头彻底切断。
这个快乐大于忧伤的院子,在二十一世纪初迫于无奈消失。那时候的农村有一个怪现象,家家户户不管有用还是没用,都在拼命盖房子,有些还是借钱盖的,盖的目的不是住人,而是等着拆迁。母亲看着他人在盖,对父亲说咱们也盖了吧,反正院子里有空地。父亲坚决不同意,说除非他死了,别想动这个念头。后来别人打起了院子的念头,母亲把我叫去商量此事,我看着父亲说,被别人占着南边终究不好,要不盖吧?父亲沉默不语。与隔壁商量后,拼着一道墙盖起了无用的两层楼房。父亲在盖房时跑东跑西,一大把年纪累得够呛。看着建成的二层楼,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冰冷的水泥块埋葬了我的童年,我的那个色彩斑斓从此消失殆尽。
据考证,姚家溯源应该在诸暨,后来分支出来到了慈溪,再到姚家斗。而据父亲说,姚家的祖宗祠堂在慈溪。父亲还对我说过一个故事。先祖原先只是一打工仔,在慈溪东家那里出卖脑力和体力。某年,东家对先祖说,现在世道很乱,你还是回家去吧,我也没什么可以给你的,送你一船麻作为银两。先祖摇着船“知嘎吱嘎”回到姚家斗。搬麻回家,打开一看惊恐不已,原来麻里有一锭金元宝,仔细检查,发现每团麻里都有一锭。先祖冷汗直冒,又不敢声张,妥善藏好后立即奔赴慈溪,想不到东家已人走楼空。清苦三年后又去,结果依然无人。先祖这才放下心来,拿出适量金元宝购置田地,修筑河埠头,建造“大屋里头”。先祖把祖宗祠堂设在慈溪,用来缅怀东家的大恩大德。我非常喜欢这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
父亲一生谨言慎行,不大喜欢说话,有些问题问他,得到的回答总是颇为含糊,不知道是想不明白还是不想说。小时候到晒场去玩,看到水泥地上用破碎的碗片儿拼成的文字“打倒刘小狗”,回家问他。他沉思很久后说,姚家斗没有“刘小狗”这个人,又说,你还小,有些事不要管。
不过,关起门来,父亲还是会小声说一些族里先人的事。他曾好几次一边喝酒一边小声说,被评成“地主”已经过世的公公(按照辈分父亲叫他公公)人挺好的,长工和雇工没钱了问他借,嘴上说要收利息却从来不要,就算还不上赖账,他也轻轻一笑不追讨的,过年了还散发红包给长工和雇工。父亲说,有些长工和雇工是逃荒来的,有些就是这个村庄的。住在村里的原来也是有地有房的,赌输了就抵押出去,而那个公公靠着勤劳和节俭买了下来,结果他变成了“地主”。“三年自然灾害”时,他虚肿着身子没东西吃,再加上生病没钱医,就死了。
父亲的话很是震撼,与教科书上的内容不大相符,教科书上“地主”总是与“恶霸”纠缠在一起。或许是姚燮故居的缘故吧,村民们颇为纯朴。在那个火红年代,“地主”的后人夹着尾巴做人,而村民说,什么“地主”不“地主”的,地都公有了还哪来“地主”?一起出工干活呗。与我年龄相仿的那几个后代,每天结伴到下邵读书,根本没什么隔阂。
我时常在想,任何物件都是有生命的,只不过我们这些俗人无从勘察罢了。“大屋里头”是姚燮先生的故居,肯定存着先生的灵气。倘若真的想祭奠先生告慰先生,就应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予以彻底修缮,里里外外的,而不是搞些表面文章。迫于无奈建造的那座庸俗不堪的两层楼房,理应拆除,这是煞风景堵心窝的俗物。
为了保护仅存的一些美好,母亲搬到镇海时,顺便从老屋搬来几件看得上眼的老家具。搁在钢筋水泥窝里,我左看右看总觉不对劲,原来它不接地气,失去了根,如同浮萍在异乡漂泊。假如某天,“大屋里头”真的修缮得有模有样,我非常愿意让它们重回故里。那里,才是它们的家,才是它们的最终归宿。
尚能些许欣慰,向姚燮先生小心禀告的是,三年前我加入镇海区作家协会后,在徐志明老师等前辈的关心指导下,已有些不成器的小文章变成铅字。儿子业已考入山东大学,学习历史学类。他此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学者。
作为三房的后人,我有这个责任,将那段已经消失的往事力求真实地予以描述下来。“大屋里头”共有四房,有待继续去挖掘探究,翻开他们的生活画卷,或许又是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
姚秉荣

姚燮故居墙门木雕刻

正在建造的泗洲寺,原为姚燮墓地旧址,姚燮墓在文革时期惨遭拆毁,坟碑砖石用于建村大会堂、仓库等建筑。

姚燮墓碑现位于村金惠莉机械厂内墙壁中
碑上镌刻“复庄姚子寿域”右旁”道光岁次庚戌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造”左旁“同配吴氏孺人
图片来源网络
姚燮(1805-1864),近代著名文学家、画家和学者。字梅伯,号复庄、野桥、大梅山民、疏影词史、复翁、老复、二石生等,清代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北仑区)人。他一生经历了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这是清帝国由表面的全盛走向全面衰弱的时代。
他有多方面的文学成就,在诗歌创作方面被后人评为晚清诗坛一巨匠,词作亦堪称清朝后期一名家,骈文创作可入清代骈文大家之列,他善写墨梅及白描人物,写意花卉,无不奇特。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很有名,尤其以戏曲、小说的研究最为突出。代表作有《复庄诗问》、《复庄骈俪文榷》、《疏影楼词》、《今乐考证》等,编有《今乐府选》、《皇朝骈文类苑》等,所著编为《大梅山馆集》传世。
长按三秒识别关注
编辑 姚 波
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3室2厅 3800元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70㎡| 2室2厅 1600元 面议 -

润泽悦溪
黑龙江70㎡| 2室2厅 2800元 面议 -

润泽悦溪
黑龙江85㎡| 2室2厅 1300元 面议 -

诗景长安
福建86㎡| 2室2厅 1500元 面议 -

领秀慧谷
海南88㎡| 2室2厅 8000元 面议 -

国风上观
黑龙江86㎡| 2室2厅 5000元 面议 -

新龙公寓
黑龙江88㎡| 2室2厅 6500元 面议 -

国美第一城
黑龙江86㎡| 2室2厅 2800元 面议 -

诗景长安
河南86㎡| 2室2厅 5500元 面议 -

山水家园
黑龙江88㎡| 2室2厅 6000元 面议 -

千禧家园
福建88㎡| 2室2厅 6000元 面议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4室2厅 250万 面议 -

青年汇
河南70㎡| 2室2厅 120万 面议 -

新龙公寓
海南140㎡| 3室2厅 160万 面议 -

智慧花园
甘肃140㎡| 2室1厅 160万 面议 -

远洋山水
河南80㎡| 2室2厅 160万 面议 -

国风上观
河南160㎡| 4室2厅 170万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85㎡| 2室2厅 150万 面议 -

诗景长安
福建70㎡| 2室2厅 150万 面议 -

远洋山水
河南160㎡| 5室2厅 300万 面议 -

领秀慧谷
海南140㎡| 3室2厅 160万 面议 -

新龙公寓
海南140㎡| 4室2厅 115万 面议 -

风格宜居
湖北50㎡| 1室1厅 49万 面议
自定义html广告位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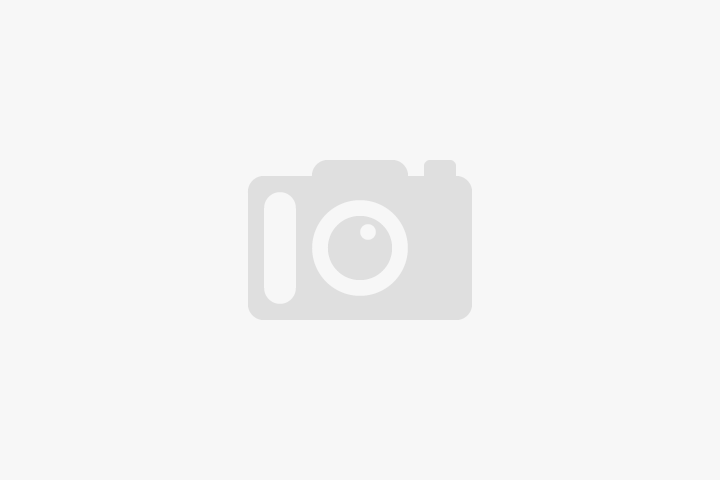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