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扫一扫

姚振函:他笔下的诗性平原 每一寸土地都为他默哀
姚振函:他笔下的诗性平原 每一寸土地都为他默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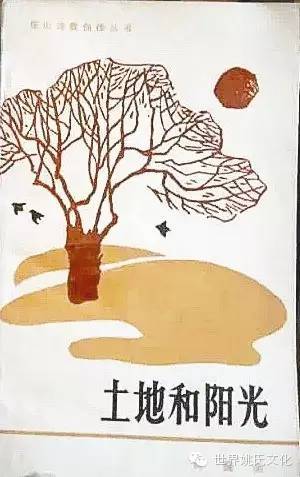
诗集《土地和阳光》书影
“这时你走在田间小道上/前边没人,后边也没人/你不由得就要吆喝一声……”曾凭《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等诗歌奠定在中国诗坛地位的著名诗人姚振函因病于2015年4月28日去世,享年77岁。姚振函是河北诗歌的标志性诗人之一,被誉为“大地诗人”,其《感觉的平原》是新时期农村题材诗歌的经典之作。姚振函逝世的消息引起诗歌圈中不小的震动,格式、郁葱等几位诗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达了对姚振函的敬佩与哀思。
“到晚年一如既往地锐利”
记者致电几位与姚振函相熟的诗人采访时,发现这几位诗人正聚在一起,协助姚振函的家属料理后事。
诗人格式在接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尊称姚振函为“姚老师”。上世纪90年代,格式和姚振函在衡水召开的中国第一届现代乡土诗研讨会上认识。“姚老师是现代乡土诗的奠基人之一,原来的乡土诗比较传统,到了姚老师这儿才有了质的改变。传统的乡土诗写农事等事物,姚老师的乡土诗不涉及这些,他写的是感受、感觉。”格式说,姚振函为人很宽厚,比他年轻一代的诗人如韩文戈等,都曾得到他的指点。让格式最为佩服的一点是,姚振函是“永远的先锋”,直至晚年,姚振函的写作一如既往地锐利。“很多作家、诗人到了晚年写作都会衰退,但姚老师的写作越来越放得开,好像无所顾忌,而且他对新生事物的接纳能力在他的同辈作家中是比较罕见的。他到晚年写作更加扎实,一如既往地锐利。”
诗人韩文戈则称:“无论从年龄还是从交情上,按说我都应该喊他‘姚老师'才对,但很多时候,他的那份朴素亲切让我情不自禁顺口喊出‘老姚'来,总之是一种父兄之情吧。我知道他不会为此怪罪于我。他是一个智慧、幽默又懂得如何与世界和解的老头。”
诗人郁葱说:“认识振函这么多年,心目中总是那个睿智的兄长,每次在一起时,他的风趣幽默总能让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振函大器晚成,他写诗的时候,年龄不小了,但一举成名。”
捕捉和审视平原上的变化
在河北省比较年长的诗人行列中,姚振函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从在1979年3月号《诗刊》发表处女作《清明,献上我的祭诗》起,姚振函几十年来发表诗作千余首。他不是高产的诗人,但他的诗深沉凝重,内涵丰富;朴素无华却颇见功力,直抒胸臆却不失之浅露;读来发人深思,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
姚振函是新时期涌现出的一位有特色、有成就、有贡献的诗人。他不仅在河北诗坛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也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诗人。姚振函从上世纪70年代末登上诗坛,尔后的20多年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
姚振函的创作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79到1985年这几年间,姚振函主要是写政治抒情诗,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反思是他的政治抒情诗的主要内容。而从1985年之后,他的目光一下子对准了农村,确切地说,对准了平原。他以诗人的眼光捕捉着、审视着平原上的种种变化。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姚振函的“感觉诗”走向自觉并达到成熟,也有人称之为“纯诗”。
真正融入土地的“大地诗人”
郁葱评价说,姚振函是河北诗歌的标志性诗人之一,“我曾经称之为‘感觉派'‘平原派'。他的诗大气、灵透、智慧、广阔,一反那种对乡村、对乡土的浅表性描摹,真正给生存的土地注入一种细致的、精致的同时也是宏大的精神气场,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开创性价值。”
郁葱认为,姚振函之所以被称为“大地诗人”,是因为他真正了解土地、融入土地,并且给土地注入一种精神气度和性格。“这样的诗人其实真的不多。振函从没有简单地记录、复制生活,没有像一般作品那样对生活作直接的‘剪影'。振函的诗看似细微、松弛其实深邃、辽远,这源于他的智慧和对诗歌的个性化的理解、感受和表达。一组《感觉的平原》成为乡村题材诗歌的经典之作,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感慨。”
晶报记者 姜梦诗
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
○姚振函
六月,青纱帐是一种诱惑
这时你走在田间小道上
前边没人,后边也没人
你不由得就要吆喝一声
吆喝完了的时候
你才惊异能喊出这么大声音
有生以来头一次
有这样了不起的感觉
那声音很长时间在
玉米棵和高粱棵之间碰来碰去
后来又围拢过来
消逝
这是青纱帐帮助了你
若是赶上九月
青纱帐割倒了
土地翻过来了
鳞状的土浪花反射着阳光
你的喉咙又在跃跃欲试
吆喝一声吧
声音直达远处的村庄
这是另一种幸福
更加辽阔
姚振函
笔名阿涛、仄之。河北枣强人。1940年1月2日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7年参加工作,2000年退休,曾任衡水市文联副主席、衡水市作协名誉主席,专业作家。著有诗集《土地和阳光》、《我唱我的主题歌》、《迷恋》、《感觉的平原》、《时间擦痕》等。作品曾获河北省首届、第三届、第八届文艺振兴奖,散文集《自己的话》获河北省作协2004年优秀文学作品奖。
晶报曾刊发他多篇随笔
大部分年轻读者可能并不熟悉诗人姚振函和他“平原上的吆喝”,但有心的晶报读者应该对他印象深刻--蒙姚振函先生赐稿,晶报《人文正刊》曾刊发其随笔《我们共同的风雨阴晴》、《品读史铁生》和《宠物》等。从这些文章中,我们读到了诗人关注人类环境和未来的大情怀,也读到了他享受天伦的小情趣。遗憾的是,斯人已逝,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读到他的新作。
2011年6月22日,晶报《人文正刊》刊发了姚振函先生的随笔《我们共同的风雨阴晴》,他从日常生活中的风雨阴晴谈起,表达了他对高科技时代人类的生存环境的关注。他写道:“人类发明了空调、电风扇、人工造雨、人工降雪、航天飞机、科学利用太阳能,人为地改变了天气、气候……使天气变化由无常变为有常,使风雨阴晴变为人类手中随意摆弄的玩偶。人类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子孙后代到底过一种什么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类未来的担忧。
作家史铁生逝世后不久,晶报刊发了姚振函先生的《品读史铁生》。他用奇特的比喻描绘自己品读史铁生的感受:“史铁生的文章像一个充气的塑料球,看似软软的,但用力一摁,摁不下去,顶手。因为它的填充物是思,既是诗,很结实,又极富弹性和张力。”
他也书写自己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在《宠物》一文中,他写自己和外孙特特养宠物的生活片段。“小兔和鸡雏,是专为外孙特特买的,特特三岁多一点,正是喜欢小动物的年龄……七八个雏鸡怎么死的我忘了,只记得它们死后那直挺挺的僵硬的双腿和紧闭的眼睛,还有外孙特特那不依不饶的哭声。”

重读姚振函
苗雨时
说姚振函是中国当代不可多得的独特的乡土诗人,其重要性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是不可替代的。即使这种评价大致不差,但如果缺乏深入、透辟的分析和解读,也仍显得皮相和肤浅。近来,重读姚振函,在深感自己过去关于他的一系列评论的此种现象学把握的缺憾的同时,忽然发现他比原来设想的要深奥得多,也丰富得多——仿佛进入了另一重艺术天地。这一发现,令人惊喜和振奋!
例如,对他的创作历程和诗歌演化的看法,一般往往是亦步亦趋的、外在的,甚至是一往无前的描述,而看不到其间的转折,乃至断裂,但正是这种转折和断裂中蕴育诗歌本体性的价值和意义。的确,他诗歌创作的走势,是步履清晰的:先是历史反思的政治性社会抒情诗,接着是深入乡土现实,在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更中,探求农村变革的深层动因,后来他以感觉潜进平原,使平原展现神秘的气韵和原始的精神脉动。这种论述,还只是表面的,追踪性质的,并没有进入它的底里和内部,因而未能发掘出诗人诗歌创作的真实的内在驱力。如果说,从政治抒情到乡土咏唱,是社会环境的变迁使然,它们仍在同一层面上滑动,那么,从一般乡土诗到乡土感觉诗,则是一种质的飞跃,对他的整个创作来说,显示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标志,就是由“回到人本身”而“回到诗本身”。单纯把它归结为主体性的确立,是空洞而浮泛的。这里的主体已不是概念的公约数,而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因而他的诗经由感觉而进入生命的深处,回归到本真的生命状态,然后在平静而自足的“美的瞬间”,获致心灵的超越和人性的觉醒。从工具性到主体性,从个人主体性到生命意识,这种诗歌本体的变化,在新时期是带有潮流性质的,但对姚振函这个诗人个性来说,此种变化则是致命的,即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诗的本质和走向。也许,至此,他才真正成为一个纯正的诗人,而他的诗也才从他的生命体验中找到了它生长发育的基因和母胎,并由此生枝、展叶,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其实,诗人在写“感觉诗”之前的诗学自白,早已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只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特别在意而已。例如,他在诗集《感觉的平原》的《自序》中曾说:在写组诗《感觉的平原》的时候,“我依稀觉得它们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在这之前我写诗八年,那些诗以外的某种实用性,那并非不正确的道理或概念,一直象阴影一样笼罩着我,我在冥冥之中遵循着它们,在它们划定的圈子里翻各种各样的跟头。为了适应,为了迎合,我必须改变本来的我”。他在另一处组诗发表的前言中又说:“在追逐了一通大气派之后,我腻烦了。我隐隐感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虚假,于是回转身来审视真实的自己。”告别外在而走向内心,摈弃概念而转向感性,拒斥虚假而重返真实,诗人找到了自我在诗中的确切位置。这可以看作是他关于诗的本体价值的真正的自觉,也昭示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源自内心的美学律令。正是这种崭新的诗学理念,催发了他感觉诗的创作。只是平行地把感觉诗和他的政治诗、乡土诗等量齐观,甚至说他不应悔其少作,显然是不着边际的隔靴骚痒。他的感觉诗的创作,是诗人自我与大平原自然的相契相合,不断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实现语言形式和能量的相互交换,从而成为以自身为目的的、超功利的、“天人合一”的蕴含着神秘意味的天籁之声。因而,它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而且,对他的感觉诗的社会学评价,也不能囿于现代“时间神话”。这种神话,“说白了就是指通过先入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在这种神话下,现在一定比过去好,未来一定比现在好。我在《姚振函批判》一文中的立足点就是这种时间的价值维度。例如,我说:“也许是诗人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为护卫自己的灵魂的独立与纯洁而选择的一种诗意栖居之所。在对抗物化和媚俗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从根本上说毕竟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逃遁。无论如何,只能说是农耕文明的一曲柔曼的挽歌。”显然,这是线性的、一维的、目的的时间价值判断。然而,这种判断,对诗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因为诗人的创作是打破这种基于进化论的时间神话的。一个真正的诗人在创作中所经验、并在作品里所呈示的时间,是一种无方向、无目的、意识绵延的、无古无今的此在的心理自由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诗人往返游荡,升降自如,他不仅在历时性中寻求活力,而且在共时性中消解和超越时间。这样的时间,是空间化的,是时间中的时间。因而,心理时间是诗歌艺术存在的自身依据。对这种时间中的诗歌的评价,不能用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来判定,只应看它表达生命的真实和深度。所以评价姚振函的诗,不能说它现代不现代,而只能说它从沉沦中敞亮了一个农民知识分子的本真澄明的灵魂。这就是他诗歌的价值所在。其他的断语,都与此无关。
也正因为这一点,姚振函的创作,特别是平原感觉诗,在河北乡土诗中,是孤愫独标的。试比较:刘章的诗的价值是历史的,他的乡土情结从意识形态中心逐渐滑向边缘,而益发沉实和深挚,他身陷其中,而无法自拔;刘小放的诗,从乡村古老的生存方式的回溯开始,在农耕文化的社会转型中,致力于建构农民生存的现代形态,他诗中的人,从小农意识的人走向现代的大写的人。而姚振函的平原感觉诗,则超越了传统和现代,进入了人的自我生命的本体,而展现了人的生存的本真状态。个体性,差异性,是艺术得以存在的根源性理由,坚持个人方式的写作是每一个诗人的本份。这里的对照,没有任何轩轾褒贬的意思,只是看他们不同的特色罢了。只要是诗都有其地位和价值。犹如花,各呈自己的香色;好似鸟,各唱自己的音调。花开鸟鸣,才是真正的春天!

从理性思考走向感觉或体验
——解读姚振函
封秋昌
内容提要:
姚振函是新时期涌现出的一位有特色、有成就、有贡献的诗人。
他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诗歌风格从最初的以理性思考见长逐渐走向对日常生活的感觉与体验。这一转变以诗集《感觉的平原》为标志,90年代之后,逐渐形成了他自成一体的“感觉诗”,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日常性、个人性、瞬间性、含混性、纯净性;这些诗的意义和贡献在于:拓展了诗歌新的表现领域和空间、做到了“感觉”和“意义”的融合、“自我表现”与“从生活出发”的统一。
一、对姚振函诗作的总体认识和评价
姚振函是新时期涌现出的一位有特色、有成就、有贡献的诗人。他不仅在河北诗坛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也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诗人。姚振函从70年代末登上诗坛,在尔后的20多年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先后出版了五本诗集:《土地和阳光》(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我唱我的主题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迷恋》(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感觉的平原》(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时间擦痕》(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 版)和最近出版的散文集《平静之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早在1982年,他的组诗《我一遍遍叩响希望的门环》在“河北省四化建设、新人新貌”文艺评奖中获得了诗歌奖(省级奖),后来,又两次获得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有多篇诗作入选各种诗歌选本。尤其收在《感觉的平原》中的所谓“感觉诗”,当年一经发表,立即不胫而走,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姚振函最初以写政治抒情诗为主,追求所谓的“大气魄”,然而,随着他对诗之“真谛”的深入探究,其诗歌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诗集《感觉的平原》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从理性思考走向具体的感觉和体验;从关注重大问题和追求“大气魄”,逐渐地把关注的目光转向琐屑的日常生活并力求残酷地“逼近真实”(内心真实);抒情主体由原来的“大我”、“超我”,向“本我”、“自我”回归;由一般的抒情诗不断地向所谓“纯诗”的境界升华。
姚振函的“感觉诗”,其意义不仅仅在艺术上达到了“纯诗”的境界,并且是一种独辟蹊径的发现和创造。他从被多数诗人所忽略了的生活角落里,从一般人认为不能入诗的事物中发现了“诗”,从无意义中发现了“意义”。因此,他的“感觉诗”拓展了中国当代新诗的题材领域和新的表现空间,同时也具有形式创新的意义。如此看来,我们说姚振函的“感觉诗”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也许并不为过。然而,诗虽“纯净”,但在诗的立意和取材上,似又过分拘泥于日常性和凡俗性,其视野相对显得有些“狭窄”和不够“开阔”。
这就是我对姚振函诗作的总体认识和评价。
二、姚振函诗歌创作的发展与变化
回顾姚振函20多年的创作历程,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就诗的内容和风格而言,基本上可以归为两大类:一般的抒情诗和“感觉诗”。因此,概而言之,姚振函的诗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段两种类型。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姚振函此阶段的诗以思考和歌唱为其主要特征。1979年3月,姚振函在《诗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清明,献上我的祭诗》,在而后两年多时间里,他所写的主要是政治抒情诗。那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刚刚从动乱和灾难中挣脱出来,正处于一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样,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反思就成了他的政治抒情诗的主要内容。他在诗集《土地和阳光》的“后记”中说:“我学习写诗的时候,正是在我们的祖国经历了一场动乱和羞辱之后。对昨天的思考和对明天的憧憬,使我忘记了自己的低能和浅薄。我无以按捺自己的感情,急于要表达自己强烈而复杂的感受,于是,我选择了诗。”因此,思考“昨天”和对“明天”的憧憬就成了他的政治抒情诗的两大主题。对于“昨天”的反思之作,当以《清明,献上我的祭诗》和《深暗的晶体》为代表。与当时的同类作品相比,其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停留于揭发、控诉或抒写伤痕,其着眼点在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防止悲剧的重演。在《清明,献上我的祭诗》中,诗人从死者“最后一瞬含恨的眼神”里,发现了死者想说而未能说出的告诫之语,即要“警惕!”警惕什么呢?就是要警惕历史悲剧的重演。而对于幸存者来说,那“带血的记忆”之所以有必要“温习”,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追思死者,更重要的是为了“祝福未来的孩子”。散文诗《深暗的晶体》最后一节他这样写道“我梦见,我蘸着悲愤和沉思,撰写烈士的墓志铭。才思敏捷,挥笔即成。/烈士从笑容里透出宽慰,我向烈士高声朗读。/奇怪!——待我定睛看时/笔下却是一部新的法典的序言。”在这里,诗人能于1979年认识到加强和健全法制的重要性,无疑是很深刻的。
1982年之后,当他看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给农村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时,一方面,他继续从宏观上歌唱祖国的未来、明天,、希望、以及为实现理想所需要的责任心、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拼搏精神,如《我一遍遍叩响希望的门环》、《我唱我的主题歌》、《纵然我们不再年轻》、《我们是对手》、《鸡鸣》、《读郎平日记》等;一方面,他关注着农村正在发生着的具体变化,特别是人的变化,即农民心灵深处的变化。他从井台上晾晒的花头巾(《井台上》),赶车人在鞭杆上精心地拴挂一绺红缨,看到了农民在不愁温饱之后,对于美的向往和追求;他从丰收场上和农民对来年的筹划中(《我家的场院》、《我看见比责任田更广阔的土地》),看到了农民的进取心和责任感;他从依然使用着旧式农具的青年农民身上(《一个农民和他的平板车》),发现了一代新式农民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和远大的眼光,在组诗《我和土地》(获首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姚振函第一个也比较深刻地揭示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新时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总之,这一阶段的诗,作者的诗思停留于理性的层面,抒情主人公充当的是“代言人”的“大我”角色,且多采取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这些诗在当时之所以能有一定的深刻性和新颖感,或是因为他所要表达的思想、认识在当时具有某种重要性和普遍性,或是因为他的认识有一定的敏感性和超前性,比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他之前还没有人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或是为一种抽象的理念找到了一种具象化的形式(如希望之于“门环”)。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些诗是力图把抽象的东西形象化,它所给予读者的新颖感是一种理性认识上的新颖感。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以诗集《感觉的平原》为代表。这是姚振函从理性的思考转向写“感觉”、“体验”的过渡性时期。
为什么说是“过渡性时期”?第一,在写《感觉的平原》之初,他只是对自己以前的诗歌观念发生了怀疑和厌倦,至于所谓“感觉诗”这一概念,可以说还相当朦胧,尚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理论上的“自觉意识”。比如,他在《感觉的平原》“自序”中说:“在写作这组诗的时候,我依稀觉得它们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在这之前我写诗八年,那些诗以外的某种实用性,那些并非不正确的道理或概念,一直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我在冥冥之中遵循着它们,在它们划定的圈子里翻各种各样的跟头。为了适应,为了迎合,我必须改变本来的自己。后来我就不能忍受了,我累了,虚假和装模作样使我筋疲力尽,我要歇息一下,摘下沉重的假面轻松地面对我所面临的世界。”为此,他想“残酷地逼近真实”,并且准备“付出代价”,因为他担心“这些诗很可能不被人们承认,从而毁掉自己在诗坛的名声。”
而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这组诗发表后很快受到一些人的喜爱”,这才使他“更加珍惜自己创作上的这种变化”了,他的“感觉诗”才越写越多。但他当时“感觉”的范围只限定于“平原”,且多属于“过去时”的感觉和记忆。第二,此时,他虽然意识到了“虚假”的可怕并想摆脱它,但他的诗歌观念并没有得以彻底改变。姚振函写“感觉诗”始于1987年2月,《在平原上吆喝一声很幸福》是他写出的第一首“感觉诗”,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收在诗集《感觉的平原》的88首诗,写于1987——1990年,其中大部分写于1987年。这些作品,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一反过去追求的“大气魄”,想要“转回身来审视真实的自己”,并且,他所“凝目”的具体对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我常常在真实和存在面前久久发呆。那些自然存在物,那些普通得毫无特色,朴实得毫无光彩的事物常常是我凝目的对象。”他又说:“在我这里,乡土和自然几乎是一回事。正是它们,引导我走向朴素、本色和纯粹。”
的确,《感觉的平原》确乎让我们感到姚振函开始走上了真实、自然、本色之路。
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还只是发生在他的“意识”层面,因为此时在他的潜意识中,对于那个“真实的自我”还是不敢大胆信任的,至少他怕别人“不信任”。具体表现为:一是尽量让“我”的感觉能够代表、传达出一般人都有的“公众意识”。比如,《在平原上吆喝一声很幸福》、《夜晚的唢呐声》、《平原和孩子》、《对露水的感情》、《平原上的一种习惯》、《麦子熟了》等等,这些诗显然是诗人“自我”的感受,但它同时又是许多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共有的感觉;二是在大多数诗中,抒情主人公实质上是“我”,但表面上经常让“你”出面,而“我”往往退居幕后。这样的诗很多,如《锄地之谜》、《平原送别》、《鼓声》、《在树下读书》、《秋天的一个细节》、《种瓜之一》……
当然,具体如何写,抒情主人公是谁,这是诗人的自由,诗的好坏也不取决于采用何种人称。但具体到姚振函当时的情况,则反映出他那时在“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犹豫状态,。这是潜意识在作怪,姚振函也许并没有意识到。第三,也正因如此,所以他此时的“感觉诗”其感觉范围只限于“平原”和往事的记忆,这显然带有实验的性质;与此同时,一些理性诗也时有所见。如《黄河作为一条河》、《H省》、《虎头山海拔八百米》、《北方致南方》、《雪北京》等,但与以前的理性诗相比,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理性诗往往直抒胸臆,这些诗则更含蓄。比如同是运用“象征”手法,在《我一遍遍叩响希望的门环》中,“门环”是“希望”的直接象征,而在上述的诗中,其中的“黄河”、“H省”、虎头山的“八百米”高度、“南方”、“北方”、“雪”显然也都是“象征”,但已不再是某种理念的“直接对应物”;就思维方式看,前者无论反思、歌唱,基本上属于肯定性的顺向思维,后者则是否定性的逆向思维。
第三阶段:90年代至现在。这是姚振函的“感觉诗”走向自觉并达到成熟的时期。自觉和成熟的标志是:对“感觉诗”(纯诗)有了自己明确的见解和标准;扩大了“感觉”的范围和空间,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有些论者把姚振函的这些诗誉为“纯诗”,而我认为把它称作“感觉诗”似乎更恰切、更能体现其特点。“纯诗”这一概念是法国诗人兼批评家瓦雷里(1871——1945年,也有译为瓦莱里的)于1920年为柳西恩·法布尔的诗集《认识女神》所写的前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当时就曾引起过较大的争论,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便瓦雷里本人,也认为所谓“纯诗”是很难达到的。他说:“纯诗的思想,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典范思想,是诗人的趋向、势力和希望的绝对境界的思想……”(《西方现代诗论》第222页;杨匡汉、刘福春编,花城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再者,就通常的看法而言,所谓“纯诗”者,并不仅仅包括“感觉诗”,它的外延要宽泛得多。但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有时也使用一下“纯诗”这一概念。
我们说姚振函的“感觉诗”于90年代逐渐走向自觉和成熟,首先是因为,他不仅写了大量的“感觉诗”,而且能结合自己的创作,把具体的经验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而这个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1987年,姚振函在诗集《土地和阳光》“后记”里是这样说的:“诗歌的价值就在于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民的感情、愿望和要求作真实的,哪怕是折光式的记录。脱离当前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却幻想去虚无缥缈的天国里或狭小的个人悲欢中去寻找所谓‘纯诗’,是没有多大出息的。”可见,那时他看重和强调的,是“人民的感情”,而对于“纯诗”,则认为属于“狭小的个人悲欢”,因此觉得是“没有多大出息的”。而他写“感觉诗”恰恰也是从1987年开始的,可见,他当时虽然意识到了应当“转回身来审视真实的自己”,但对这个“真实自我”的价值何在,却是不甚了了的,那么他担心不被别人承认,怕“毁掉自己在诗坛的名声”,就是很自然的了。当他的“感觉诗”出乎所料地“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并且积累了相当的创作经验时,到1994年,对“纯诗”,才有了如下的理论概括:“我对纯诗的界定是:“纯诗,就是在诗中除了诗以外,再没有非诗成分的那种诗。再具体一点:纯诗是人的心灵直接面对存在并感应存在的结果;纯诗中只有纯感觉,没有理性的判断性表述;纯诗没有劝世、教化等直接功利目的。”那么,“纯诗”有什么意义呢?他借用了别人说的四个字:“安顿生命”(散文集《平静之美》第31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姚振函的“纯诗”论,不是来自书本和他人的经验,而是对自己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其次是感觉范围和空间的扩大。这只要看一看收在诗集《时间擦痕》中“境遇”、“乡土与人”、“零乱的抒情”等部分的诗,就不难看出,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感觉”已经远远超出了乡土和平原:农村、城市、本地、外埠;楼房、树木、月色、牛、羊、飞鸟;骑车、散步、看书、睡觉、聊天、静坐、看电视,等等,等等,凡是诗人心之所想、目之所见、足之所至、耳之所闻,统统都能进入了他的“感觉”视野,而且这诸多“感觉”,为“诗人自我”所独有,那个“超我”的影子和所谓的“公众意识”也已销声匿迹;被他所“感觉”的具体事物,确乎已经属于那种“普通得毫无特色,朴实得毫无光彩的事物”了。
再次,到90年代中期,姚振函的“感觉诗”形成了自己比较稳定、鲜明的特点。下面还要单独论述,这里从略。
三、姚振函“感觉诗”的特点、意义及局限
姚振函进入成熟期的“感觉诗”,其感觉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展,几乎涉及到他的所见所闻的方方面面,大体可以划分这样几种情况。(一)对客观物象的感觉。如在《楼与楼》、《树的响声》、《冬天的月亮》、《两个城市》、《仰望一棵树》等诗中,对楼房、月亮、树木、城市等客观物象的感觉;(二)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感觉或微妙的心理状态。如《敲门声》、《初到异地》、《你住过的楼房》、《久居城市》等;(三)诗人在瞬间的一种思绪。如《火车经过红土山坡》、《友人的背影》、《下雨时想念外面》、《外面下雨》、《窗户》等;(四)对某一情景、事件或过程的感觉。如《旅行》、《黑暗中的楼梯》、《一种经历》、《隔河相望》、《和朋友同室而眠》、《一位年轻的孕妇在电车上》、《砍倒一片玉米》、《任南风吹拂》等;(五)一种习惯性动作或劳作中的一种神态。如《早晨的天气》、《窗户》、《掘地的人》、《乡土与人》中第9首、10首、13首、14首、16首,或写一种劳动过程和姿态,或写做某一动作时的神情,或是对一种动作的剖析等等;(六)写回忆往事时的情态和感觉。如《回忆月亮》、《往事》、《往事中的遗憾》、《想念白房子》、《种一棵树》等等。
由此可见,不同的物象引起了诗人种种不同的具体感觉。但在这不同的“感觉”中,也有一些内在的一致性和共同的特点,这就形成了姚振函的“感觉诗”的总体特点,即1、日常性;2、个人性;3、瞬间性;4、含混性;5、纯净性。所谓日常性,是指被诗人所“感觉”的事物,纯属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微不足道的琐事,它既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没有明显的教化目的,但分明又含有耐人咀嚼、值得玩味的某种“意味”或情趣,即是具有“诗意”的。所谓个人性,是说抒情主体已无意充当公众“代言人”的角色,其“感觉”纯系诗人的“自我”感觉,这个“自我”,也不再是那个“超我”和“大我”,而是那个真实的“本我”或“真实的自己”,是那个真实的“自我”在直接面对其“感觉对象”(存在)时,被感觉对象所激发出的一种“有意味”的主观感受:或是一种情绪,或是一种情调,或是一种心态,或是一种情境,或是一种氛围;诗人又是忠实于这种“自我”感觉的,他不迎合,不投其所好,不媚俗,不伪饰,而是把自己的“感觉”如实地予以表现。所谓瞬间性,是说被诗人表现的“感觉”,并非是一种恒定不变的存在,诗人所捕捉到的,是诗人在面对存在时,在一刹那间被激发出的“感觉”。所谓含混性,是指“诗意”的朦胧、含混、多义和难以解释。他分明让你意识到了什么,你却一时难以找到准确的语言来解释它;它分明唤起了你的某种经验和记忆,你很想为它补充点什么,却又不知该补充什么。所谓纯净性,是说诗人能把他感觉到的“诗意”或“诗性”,用最简洁的形式凸现出来;能够把一切非诗的因素、多余的东西、似是而非的东西最大限度地予以排除。在一首诗中,非诗的东西越少,诗作就越“纯净”。“纯净”,是诗人艺术表现力的体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姚振函的“感觉诗”中,上面提到的“五性”,是很难拆解开的,它们往往在同一首诗中同时存在。比如《火车经过红土山坡》这首诗,就是诗人在火车上看到一个农民在黄昏时扛着镢头向红土山坡走去时,刹那间产生的揣想和思绪,你分明感到了内含于其中的“诗意”,然而这“诗意”又让你觉得含混和难以说清楚,因为它是丰富的含混,可以激发起不同人的不同心绪及其想象。
前面已经提到,姚振函的“感觉诗”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不能低估。首先是开拓了诗歌新的表现领域和空间。虽然意象诗和以表现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诗早已有之,但对琐屑的日常生活进行集中的全方位的“凝视”和观照并自成一体的“感觉诗”,在中国诗坛上,姚振函可谓是首开先河者,而且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接近了所谓“纯诗”的境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对那些假、大、空的诗风,是一种有力地“反拨”。其次,姚振函的“感觉诗”做到了“感觉”与“意义”的融合,或者说,将“意义”寓于具体的“感觉”之中。因此,姚振函的感觉诗能够作用于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层面,体现为一种陶冶情操、“安顿生命”的审美价值。就中国的新诗来说,像这样具有审美价值的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为,现在有些所谓题材重大的诗,非诗的东西太多了,它们充其量只能作用于人的认识和理性层面,它所发挥的所谓“教育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这些表面看来意义不大的“感觉诗”,并非真的没有意义。再次,姚振函的“感觉诗”把“表现自我”和“从生活出发”统一了起来。诗人要不要“表现自我”?要不要“从生活出发”?回答都应当是肯定的。但是,有些人常常人为地将二者对立起来,或者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或者强调后者而否定前者。有些强调“自我表现”的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表现的“自我”,即作品传达的思想和观念,多属从洋人那里趸来的,并不属于他自己的感觉和体验,所谓“自我”表现,其实所表现的,并非货真价实的“自我”。姚振函的“感觉诗”完全基于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真切感觉和体验,其“诗意”与激发诗意的具体物象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姚振函的“感觉诗”既是“自我”的,又是相当生活化和本土化的。所以,著名诗人牛汉说得好,姚振函就是姚振函,“任何主义都与你无关”。
在充分肯定姚振函的“感觉诗”的前提下,我们也要看到其局限和不足。概括起来讲,我以为是“小有余而大不足”。我这里所说的“小”和“大”,不是指问题或题材的大与小,而是指作品的题旨和内在意蕴。诗人既可以把“大题材”写“小”,也可以做到“小中见大”。关键取决于诗人主观“感觉”的质量。对“感觉”不能一概而论,有在较高层次上的“感觉”,也有低层次的“感觉”;有深刻的“感觉”,也有肤浅的“感觉”。因此,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写“感觉”,要看是什么样的感觉,即“感觉”的质量如何。姚振函虽然把自己的“感觉”拓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与生活的广阔性相比,“日常生活”也仅仅是它的一个角落,毕竟属于一种“狭窄”。对于姚振函来说,现在需要放飞自己的“感觉”,在对“日常生活”的感觉和体验中,需要有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在更高层次上达到一种形而上的抽象,千万不要仅仅满足于对“日常生活”的“感觉”。
否则的话,怕是难有新的突破和新的进展的。
总之,姚振函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示,最突出的是这样两点。第一点,一个作家,要想保持长久的艺术创作活力,就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需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自我超越的愿望并付诸具体的创作实践。具体到姚振函来说,就是勇于摘掉“面具”,敢于去面对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自己。第二点,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文学观念”之于一个作家的至关重要性。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或者说,作家的文学观念,决定着作品的具体面貌。姚振函为什么会发生上述的变化(从写政治抒情诗到——农村诗——又到感觉诗)?文学观念的不断转变使然。正确的并且是适合于自己的文学观念,能够促进创作的发展,反之,就会落伍,就会无情地被淘汰。
虽然姚振函已逾花甲之年,但对作家而言,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似乎更重要。因此,我们希望并且相信,姚振函在诗歌创作上一定能够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和自我超越。
姚振函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1967年参加工作。历任衡水市文联副主席,衡水地区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衡水市作协主席。专业作家。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诗集《土地和阳光》、《我唱我的主题歌》、《迷恋》、《感觉的平原》、《时间擦痕》,诗歌《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等。诗歌《我和土地》、诗集《感觉的平原》、诗集《时间擦痕》分获河北省首届、第三、八届文艺振兴奖,散文集《自己的话》获河北省作协2004年优秀文学作品奖。
长按三秒识别关注
编辑 姚 波
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
自定义html广告位
-
下一条:虞舜终身孺子慕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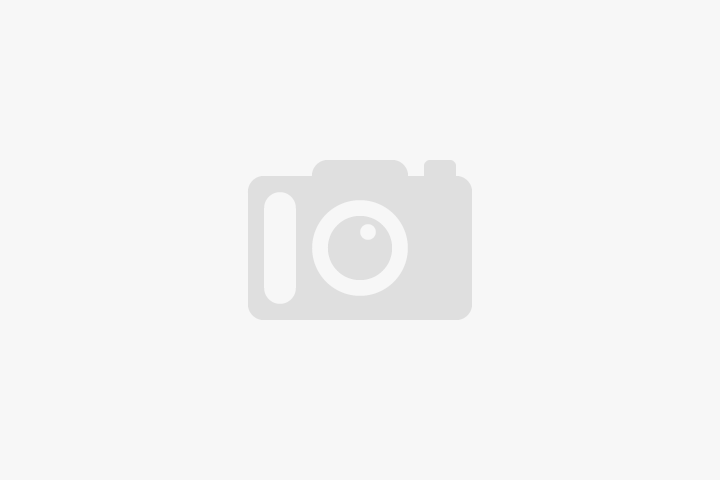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1739